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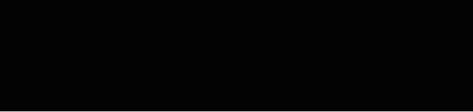
夜色的黑暗,那不是黑暗,而是人们无穷无尽的争端,将你我推向了最远两端——异端。
——五月天《少年他的奇幻漂流》
他在星空下睡着了。他的羊跪伏于荒草之上,低沉的呻吟声是对主人最后的告别。帕克萨的星际,有一个十六岁的灵魂长眠。或许应当说,是永恒地镌刻。
他出生于斐曼城的哈拉村,出生那天,暴雪袭城。斐曼城人祈见阳光的第二十天,却迎来几十年一遇的天灾。窗外的雪愈堆愈高,甚至湮灭了地平线直冲天际。父母望着怀中这个满脸通红的小男孩,为他取名“苏迪”——在斐语中,是希望的意思。他是这个家的希望,也是,尼克族的希望……

从三岁起,苏迪便跟着祖父一起放羊。祖父领着羊,苏迪拉着祖父的衣角,从哈拉村的西头走向哈拉村的东头,坐在高高的草垛上眺望远方的齐尔顿——帕克萨的另一座城市。祖父叼着雪茄,将羊鞭插进长筒靴,眯着眼为苏迪讲起过去的故事。白昼到黑夜,又从村东头到村西头。苏迪的童年,是羊背上啃不完的面包,是梦里见过了无数次的祖母。与祖父而言,斐曼城是生命的全部,是一辈子的死守。可苏迪渴望远方,他想去齐尔顿看看,想去更远的地方。但他是斐曼城人,更甚于,他是尼克族人。

战争是冷酷的。突如其来的炮弹打穿斐曼城的宁静,不一而足的爆裂声刺破的是斐曼城和切尔顿最后一线平和。苏迪已成少年,那年,他十岁。二城归一国,二城为异族。外敌的侵入日渐猛烈,哈拉村的劳动力们被迫上了战场,苏迪的父母也在其中。父母的离去,意味着苏迪一个人的留守。三年前,祖父在睡梦中离世,他似乎早已意料到自己走到了生命尽头,那双伴其数年的马丁靴里塞着一封信。苏迪好奇极了,可父亲却说什么也不让他打开那封信,此事只好作罢。祖父离去后的夜晚,苏迪的梦中常常出现远方,不只是齐尔顿,还有海的彼岸,许许多多他从未见过的地方。

他十一岁,他只身一人。外战没有结束,内战愈发猛烈。少年苏迪在长大,他在找寻,找寻未知的未来。祖父走后,羊群不再,唯留一只嗷嗷待哺的雏羊与苏迪为伴。斐曼城的冬天,很难见及阳光。某天傍晚,苏迪与幼时一般倾靠在草垛上,冥想着无数无数的可能。他进入了梦乡。那个已经数不清出现多少次的梦如汹涌洪波冲击着他混乱的心,命运的罗盘仿佛在告诉他应该驶向的远方。那是苏迪的祖母——他从未见过的祖母。三十年前斐曼城和齐尔顿的异族之战打响,斐曼城里的许多外族人为了民族的威严,不惜告别至亲归家。这一别,即是祖父和祖母的一辈子。当然,这些都是祖父说起的。祖父是痛恨的,他不断谩骂着那些不团结的国人,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人民却因为民族的歧视而互相伤害。但他终究是尼克族人。爱情在民族面前灰飞烟灭,他不允许自己去见爱人,因为这在他心里意味着对民族的背叛。幼时只听事中人,少年忽意事中境。祖母模糊的脸庞在苏迪的梦里不停地浮现,她用熟练的斐语不断呼唤着苏迪的名字。夜很短,短到苏迪留不住祖母的慈爱。他在破晓前醒来,他在黎明前沉思。苏迪敬重祖父祖母,但他不明白长辈为何如此矛盾。民族和爱只能选择一者吗?血脉的交织为何在歧视的风暴中渐疏渐离?
十二岁的冬天,是不幸的。从战争中有幸逃离回家的邻居告诉苏迪,父母牺牲了。不是那烽火连天的外战将他们掳去,是齐尔顿喀斯族人无情的枪弹。数百年来,喀斯族人从未从“尼克族人是下等人”的思想中脱离,他们看不起“下等人”,即使是这与外的生死攸关,他们攻击的心依旧强烈。“我们彼此存在,为何彼此相害?”少年苏迪不断发问,可他没有答案。一场暴雪,哈拉村被长久的黑夜笼罩。苏迪感到了莫名的熟悉感。他收拾好行囊。虽然他分不清彼时的白昼与黑夜,但他要牵着羊走向远方。他要去寻找和平,寻找异端的平衡点。

苏迪在走,走过战火纷飞的国度。他来到齐尔顿,他踏遍每一个村落。“我是尼克族人,我可以借宿于此吗?”一家一户的门被敲开,又一家一户的窗被掩紧。齐尔顿人民的眼底写尽了冷漠与鄙夷,夜色黑暗将人性的两端推向无垠的边际。苏迪在前面走,羊在背后踱步。十二岁的少年想要尽一己之力去改变国家的变乱,可他只是十二岁的少年。他也想家,家却永远不在了。倘若说人活着需要精神支柱,苏迪又何尝不曾缺失最大的底气?羊蹭了蹭他的腿,苏迪停下了脚步,缓缓坐下、躺下,最终蜷缩于冰冷的沙地上。苍穹之下,孤傲的风吹散了歧视,它与苏迪的心一齐把歧视揉碎,葬入风浪肆虐的大海。哦,还有那封信,离家前取出的那封信。苏迪如梦初醒。
“亲爱的苏迪,祖先保佑你尚还安康!祖父想跟你说说话。我老了,注定要离去,你不必心伤。记得小时候吗?我时常对你讲起齐尔顿的祖母,哦,她真的是我一生的心痛。我不是冷血,不是高傲,我也想与她相会、相守。但是喀斯族人对尼克族的鄙视不允许我这么做。我的父亲曾是尼克族的族长,他在与喀斯族人的战争中不幸离世,这也是我一辈子的痛与无奈。哦,小苏迪,我真的没有办法做违背民族尊严的事。还有那群羊,我为什么要养羊?我真是困难极了。我无法与你的祖母相见,通信也被阻断,最后我只能想到‘羊’——在喀斯语里是团结的意思。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族部战争能停止,两族人能够和睦相处……亲爱的苏迪,你一定要好好的。”

少年年少,少年也是鲜衣怒马。十三岁的苏迪带着小羊继续行走,他走出了齐尔顿,走向了更无尽的远方。他不再拘泥于言语上的寻求和平与友好,他在天南地北帮助有需要的人,他想告诉所有歧视他们的民族:让世间充满爱。不仅是喀斯族。
一年、两年、三年……少年还是少年。苏迪在等待异端的相交,苏迪欣喜于羊的长大。他继续流浪,流浪于争纷的路口,偶尔短暂的归宿是心灵莫大的慰藉。十六岁那年的冬天,苏迪置身于不知名的远方,他在荒草上仰卧,羊低着头,细细咀嚼。夜很长,长到大雪纷飞。只是这次,苏迪再也没有醒过来。他一定累了吧。
还有那只羊。羊还在,和平不远了吧。

注:本故事的人物、地点、情节等纯属虚构。
谁生错血脉?谁长错色彩?谁梦错了期待?……当你抬头看,何时那万种渐层的斑斓已默默绽放在黑夜终端。
——五月天《少年他的奇幻漂流》
星空璀璨会带走黑暗,汪洋交汇是人类血脉的拥抱。愿世界和平,愿无数的你我热情相拥。
Copyright© 2020 文化传播学院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