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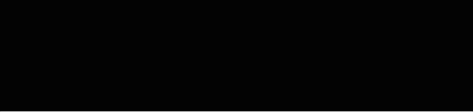
“艺术对于艺术家就像呼吸一样,你不会质疑呼吸,你一定会呼吸,不然就会死掉。如果你早上起来有一些想法,然后你将这些想法变成某种强迫的意愿,不得不创作,你绝对是一名艺术家,但这并不代表你是一名优秀的艺术家。你仅仅是一名艺术家。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你控制不住你自己,像是鬼迷心窍一样,不是艺术在你的脑海里然后去理解作品而已,是将你的作品做一个强烈的错综复杂的整合。还有我认为一个艺术家要时刻做好失败的准备。但并没有很多人这样做。”这是让我非常信服的话,迈克尔·基默尔曼也在其《碰巧的艺术》里说:艺术不该是一份工作,而是生活下去的必需品。
玛丽娜和乌雷的结合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作品信息:
1974年
节奏系列终结作品《节奏0》
意大利那不勒斯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是这个名字你听起来可能陌生,但你肯定知道数十年前的纽约,办起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展览——《节奏0》,这件作品为她成为“行为艺术之母”奠下了坚实的基石。玛丽娜放下人权,把身体交给观众,六个小时内他们可以用提供在桌子上的七十余件物品对她做任何事,那些物品里有玫瑰、口红,有刀、枪、子弹、菜刀、鞭子……玛丽娜告诉大家这段时间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她自己承担。她成功了,人的本性浓缩于她的身体,以令人惧怕的方式。在六小时实验以一人持枪塞进她的嘴巴而告终时,她的上身已经全裸,石膏粘合着她的伤口,玫瑰的尖刺上还残留着她的血滴。当她恢复为“人”的时候,人们四处逃散,胸中的意识重新觉醒,他们害怕承担后果,害怕道德的谴责。每个人的胸中都有一头困兽。人权是当事人说没有就没有的吗?人权是客观的存在,是永远保护、也永远约束着我们的存在。玛丽娜差一点就失败了,不,应该说她太容易失败了,只要一支小刀割断动脉,只要那嘴里的枪被扣动扳机,名为“她”的这份艺术就真的会从世界上消失了,她真的像其所说的那样做好了失败的准备。这副作品本意不在于揭露,而在于警示,人性就是这样,社律永远存在,看你怎么选择。

艺术的产生一定源于某种创造的冲动,源于某种深层的被纵容到了极致的不可抗力。玛丽娜所展现出来的自由就是她在童年里拼尽全力想得到的,她突破传统的极致表达方式也是她命运的选择,而世界上还有一个和她相似的人。
乌雷·赖斯潘

要说乌雷·赖斯潘,他是先锋艺术家,是敏感、自由的灵魂,勇敢的时代先驱。千万不要陷入“艺术家都不善交际”的误区。像乌雷,他深谙与群众交流的方法,他的拍摄对象多为社会边缘人物,当他用宝丽莱为他们摄影时,他会把第一张成片送给被拍摄的人,这是艺术家和群众建立联系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也是能让被拍摄人更容易接触、更愿意配合的好办法之一。在行为艺术中,群众不只是艺术传递的终端,他们还是艺术的重要部分,艺术的创造者之一,一旦你发现并承认了这点,你的艺术作品必能获得震撼人心的潜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们认识了彼此,那时的乌雷高大帅气,他一面是男性的粗野装扮,一面是没有胡须浓妆艳抹的女性装扮,十分迷人且特立独行。1975年11月30日,玛丽娜29岁生日,她受邀去阿姆斯特丹表演一个行为艺术。乌雷作为指派助手,去机场接她。两人第一次见面,就被对方深深吸引。因为他们太像了,像是失散多年的兄妹。都是先锋艺术家,都留着长发,连扎头发的方式都一样。都是射手座,那天还都是他们的生日,他们交换日记,发现对方都把11月30这页撕掉了。此后两人在床上呆了十天……他们就这样相爱了。
他们震惊我的第一件作品是《挑衅,对艺术作品的非法接触》,乌雷迈着大长腿快速地走到19世纪画家卡尔·斯皮茨维格的作品《可怜的诗人》面前,他摘下画,在玛丽娜的拍摄下完成了偷盗的全过程。原来在艺术家眼里法律不过是艺术的表达工具之一。
在长达十二年的爱情碰撞中,他们还创作出了非常多的作品,像他们的爱情一般,其作品每每问世都会激起一阵轩然大波。

1977《时间中的关系》:时间流逝,爱的臂膀更加用力,捆绑成为爱的附加品。

1977-1978《呼气》:他们堵住鼻子,用彼此口中的空气相互支持,直到17分钟后两人因填满肺部的二氧化碳双双晕厥。只有彼此作养料的爱情支撑不了多久,只沉浸于两人世界的亲密关系很快就会枯萎。

1980《潜能》:玛丽娜的行为艺术从来都是以牺牲为保障的,这件作品中玛丽娜手握弓,乌雷持箭对准她,箭已擦上毒药,两人反方向用力,支撑起彼此的身体,观众们可以看到两人的心跳越来越快。玛丽娜又一次把命交给了别人,交给了艺术。

再激烈的灵魂碰撞也还是面临了危机,他们决定以《情人·长城》这组作品来作为分手仪式,两人一个从嘉峪关出发,一个从山海关出发,各自历时三个月,走过2500公里,在长城中央相拥而泣。“我想,上帝啊,我失去了我的男人,我爱我的艺术。”艺术是信仰、迫不得已的欲望,这件作品他们计划了很久,本来打算完成之后就去结婚的,没想到却成了分别前最后的仪式。
冒险→碰撞→表达→冒险→碰撞→表达……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艺术要用生命的跨度来衡量,行为艺术就是这样,艺术家已经离世,观众们的创作却还在继续,他们不断解读,不断挖掘,不断赋予幻想,不断注入新的时代意义。他们先把自己活成了艺术本身,再把彼此的结合也变成艺术,用艺术的方式相遇,用艺术的方式分离,用艺术的方式死去,用艺术的方式忍受孤独。


最教我吃惊的不是他们为爱痴狂,不是他们把一生都献给艺术,而是他们的克制和冷静,艺术家总是狂热而忘我的,但玛丽娜和乌雷却时常能从疯狂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客观地对待彼此的亲密关系,这不是每一位杰出艺术家都具备的特质。当二十二年后他们在纽约重逢的时候,玛丽娜抬头,乌雷就出现在面前,我难以想象当数年的时空阻隔骤然变成了眼前熟悉又清晰的脸时,克制住自己的情感,只是深深对望默然不语是什么感觉。2015年乌雷以侵权起诉了玛丽娜,两人共同创作的作品被放入了阿迪达斯的广告中而他并没有得到版权费。可能你会觉得既然相爱谁还会在意版权费呢?但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是再正确不过的事情了,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观念要求别人。正是因此,他们的爱情只是爱情,不掺杂任何杂质。2020年3月2日乌雷去世时,玛丽娜发布的动态像极了一个普通朋友会说的话,口吻更像是客观的新闻报道,可能是因为我——作为一个观众出自本能的窥探欲吧,我渴望挖掘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悄悄话。“今天我非常悲伤……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值得深刻铭记的人。”她只称他“friend”“partner”,过往的灵魂碰撞震荡在深处,言语在这面前一文不值。

我在振奋人心的艺术和爱情面前语无伦次,我看着他们狂笑,看着他们流泪,我在他们的故事里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要说乌雷和玛丽娜的感情,是无法单单归类于“爱情”的,他们是伙伴,是密友,是灵魂伴侣。而这个世界上的感情,同样错综复杂,简简单单一个“亲情”“友情”“爱情”怎能分得清?

Copyright© 2020 文化传播学院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