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位视障人士在导盲犬的辅助下攀登泰山的事迹引发争议。人们在感叹残障人士勇于突破身体限制、追寻生命高度的同时,也对导盲犬在此类高强度登山活动中的职责范围提出了合理关切。这背后触及了几个深层议题:残障人士的平等出行权、工作犬服务范围的界定以及公共服务体系的管理责任。同时,它也促使我们思考:在推动社会包容的同时,我们应当如何实现权利与责任、人与动物之间的价值平衡?

图源自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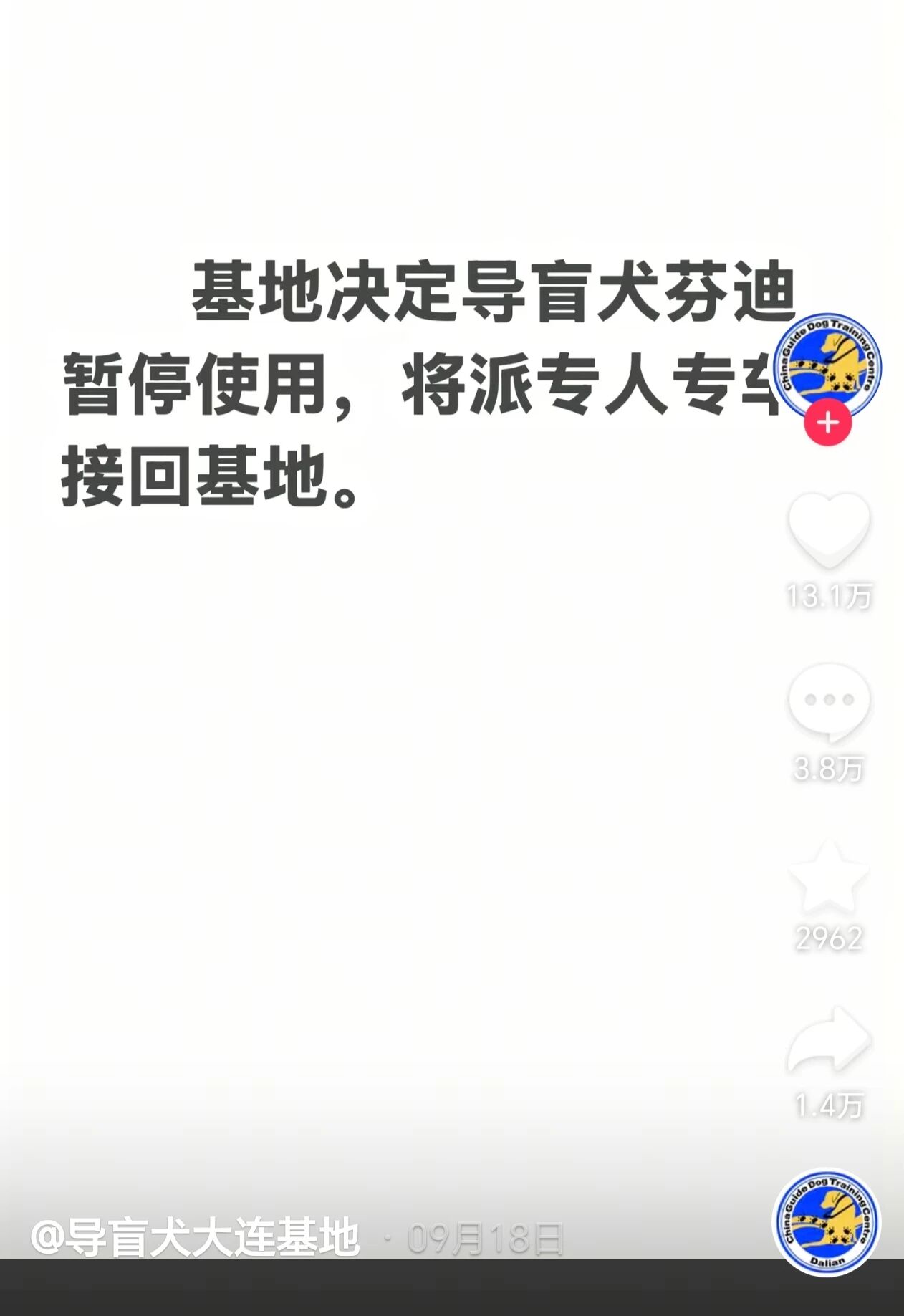
图源自网络
首先,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肯定,视障人士依法携带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赋予的法定权利。当事人携导盲犬攀登泰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生命的坚韧意志,是视障人士平等出行权在现实场景中的一次生动实践。这份对平等权利的追求固然值得我们尊重,但泰山向来以险峻多石、气候多变著称,对常人而言已是不小的挑战,更何况视障人士与导盲犬。这种高风险场景下的权利践行,自然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而公众对该事件的关切与担忧,正源于对其中潜在风险的理性审视。
公众的关切与担忧,本质上是人们对导盲犬的生命关怀与对景区公共管理能力的理性思考。一方面,出于对导盲犬作为特殊工作伙伴身体健康与长期福祉的切实考量。泰山阶梯陡峭、路程漫长,持续的攀爬可能对犬只的脚垫、关节乃至心肺功能构成巨大挑战。人们的这份关切,已然超越了将导盲犬简单视作功能性工具的认知层次,体现出人们保护动物意识的深化;另一方面,这份担忧来自人们对公共安全与景区管理压力的审慎评估。在游客密集、地形险峻的环境中,导盲犬的工作状态,是否会因体力透支或外界干扰而下降?一旦发生意外,景区有限的应急救援资源又能否有效响应?这些疑问并非苛责,而是对潜在现实风险的负责任审视。
由此可见,公众质疑的内核并非限制权利,而是希望在“人的权利”与“动物福利”、“个体探索”与“公共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平衡点。

图源自网络
而要找到这份平衡,关键在于让普遍共识适配具体情形,进一步优化社会的规章制度,从而实现权利保障与风险防控的协同。若我们将“导盲犬可自由进入公共场所”视为普遍共识,其实施细则就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场所的环境特点与风险等级。将日常的商场、地铁与海拔超1500米、阶梯逾7000级的泰山画上等号的行为,无疑是忽略了不同公共场所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尤其在我国,导盲犬仍属于稀缺的公共资源。全国现役的导盲犬仅数百只,每一只都经过长达数年的严格训练,其核心使命是服务于视障人士日常的独立出行,如规避障碍、识别路口等。它们是视障人士在城市中得以安全通行的“眼睛”,而非攀登高耸山峰的“登山杖”。将如此宝贵的专业资源投入远超其常规工作负荷的高风险环境,不仅可能影响导盲犬的工作寿命,更可能对使用者及犬只本身构成潜在的巨大伤害。因此,我们有必要依据各类公共环境的风险系数、导盲犬的体力负荷状态等客观指标,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管理细则,对携带导盲犬出入不同公共场所的行为加以规范。这不仅能使视障人士的平等出行权落到实处,也能使这一权利的保障更具可持续性。
更进一步说,要建设一个真正温暖的文明社会,绝不只是在于个人权利的行使,而在于我们对权利边界的审慎思辨。这场争议的深层价值,恰恰在于推动我们超越个案本身,审视背后权力、责任与安全的复杂关联。我们必须明白,导盲犬绝非普通宠物,而是经过系统训练,用于维系使用者安全的工作伙伴。将二者混为一谈,只会模糊讨论的焦点,使导盲犬的特殊价值难以被人们所正确认知。在此背景下,公众对本次事件的关切实则是反映出人们对两种极端倾向的警惕:一方面,我们应避免陷入“权力绝对化”的误区,即防止因过度强调个人选择而忽视了动物福祉与公共安全;另一方面,我们也须警惕“极端动物保护主义”的情绪化指责,这种倾向有可能会在不经意间造成以保护之名行伤害之措,进一步压缩残障群体来之不易的自主空间。
事实上,一个真正无障碍且充满关怀的社会,其内涵远不止是在于权利行使的畅通无阻,更在于人们对共同体中每一个生命体的尊重与深切关照。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捍卫视障人士平等出行的社会权利,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的权利实践,不应也不必建立在对其他生命长远健康福祉的过度消耗之上。
归根结底,制度的完善,需要的不仅是冷冰冰的条文,更要有热腾腾的共情。一份真正落地的导盲犬准入细则,不只是规则的补全,更是检验治理格局的试金石——在秩序中留出温度,在包容中实现共生。当规则的刚性与人情的柔软真正交织,我们所期盼的包容社会,才不会只是停留在口号里的空想。
Copyright© 2020 文化传播学院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