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提升强化研究生培养质量,2024年5月29日晚6点半至8点半,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研究生主办、文化传播学院承办的增光传媒前沿论坛“传播与社会发展”学术讲座活动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本次讲座主题为《因地制“仪”: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与乡村传播网络重构》,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何志武主讲,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吴麟老师主持,文化传播学院全体研究生、部分本科生,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师生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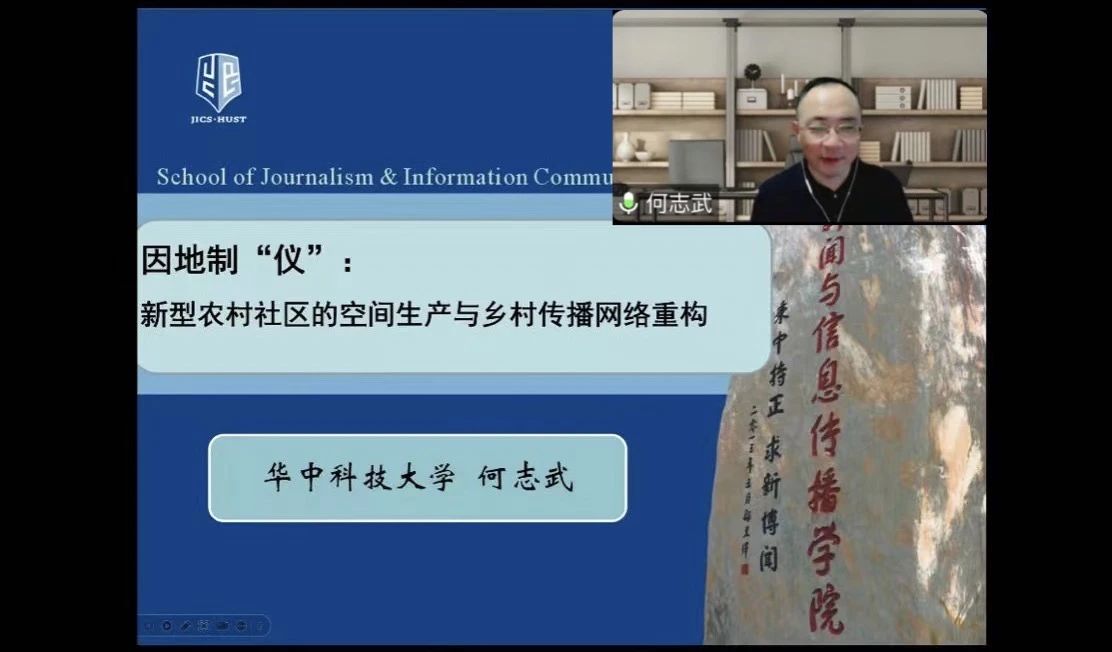
在中国,乡村话题具有特殊的意义。传统乡村的印象低矮的房屋与泥泞的小路。新世纪以来,基于空间生产、迁移、再造的新农村建设和新型村镇化画卷在中国乡村大地徐徐铺开,道路、房屋、公共空间、公共设施……村民居住空间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散落的村庄到集中居住的农村社区。讲座中,何教授综合前沿理论与田野材料,以传统村庄和现代乡村的对比为出发点,提出:空间的生产和空间中的个体实践是理解当地政治、文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是洞察地方治理逻辑、权利结构的据点。
何教授团队多次到位于湖北省钟祥市西南部的H村进行调查,提出一系列创新性问题:农村社区如何根据自身特色生产公共空间,这些空间具有哪些仪式化的意涵,媒介是如何嵌入其中的,空间中的仪式符号是如何被建构的?在农村社区不同公共空间中,传播的实践是如何展演的,其中的互动机制是怎样的?这种空间生产和传播实践之于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活观念和社区治理的意义,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围绕这些问题,何教授以H村的研究为例,分享了以下的研究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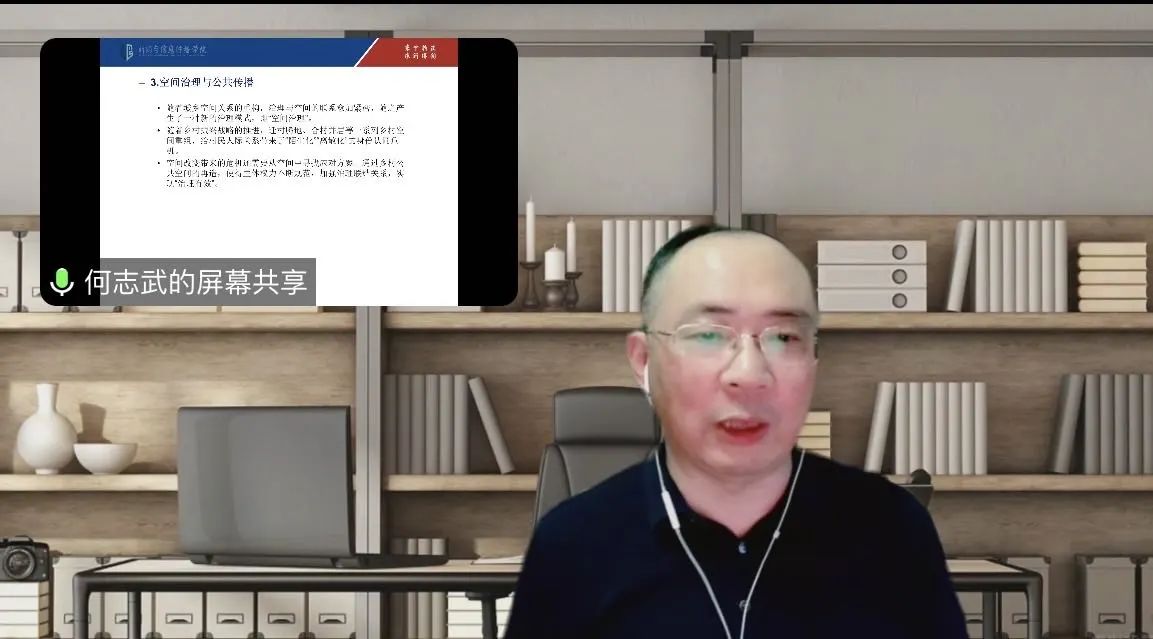
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生产:空间驯化了村民的仪式化生活
无论是工程搬迁、扶贫搬迁还是撤并搬迁,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格局皆统一规划,整齐排列,风格统一,一改以往农村房屋散而乱的外观符号,凸显新农村的美学色彩。这些新型农村社区地处乡村,因农民集中居住而成为一个集镇式的小区。社区功能齐全,有宽阔的水泥路、明亮的路灯、多功能广场,还有房前屋后的晒场、菜园。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设计保留了传统农耕社会的底色,更加入了现代城镇社会的空间元素。空间生产不仅筑起了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场所,更生产了联结乡村邻里的仪式符号,超越实体空间的仪式化空间随之产生。
邻里交往空间的拓展:打造“可沟通性”新型农村社区
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有组织的集体生产就不复存在,农业生产成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村民间基于劳动协作的交往几近消失。分散的村庄格局限制了村民的交往,村民的交往多限于村庄内的左邻右舍,分散的村庄成为可沟通性不足的代名词。新型农村社区虽并未改变农村的生产模式,但生活空间的变化改变了村民的交往空间、交往实践和交往内容,基于交往的可沟通性农村社区得以建立。
“传统媒介”重启与新兴媒介激活:乡村传播网络重构
正如德布雷所言:“我们生活在媒介圈中,就如同鱼在水中一样自然,浑然不觉。”在不同类型的新型农村社区,居住空间、娱乐空间、运动空间中被植入多元媒介,一些传统媒介被重启,新的媒介也被激活,重新建构了一套乡村传播网络。
治理效能的提升:建构主体间性的社区治理
空间生产是基础,公共传播是中介,社区治理是目的。H社区的空间生产带来了居民交往方式、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的变化。这些改变或显性或隐性、或短暂或长期地改变了H社区的治理方式。空间、传播与治理三者关系不是线性、单向的递进,而是三角闭环的相互转化。依托于新型社区的公共空间开展有组织的村民议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公共性的建构。
最后,何教授指出,横店村从空间生产中找到密钥,通过仪式化的空间,强化社区内部的“可沟通性”和自我认同以及外部的“可见性”和他者认同。通过空间的中介连接,织起了基层社会公共传播和社会治理的行动者网络。我们应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说到底,是要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多方资源,激活基层百姓的主体性、积极性、连接一切可以连接的资源,而连接的关键环节离不开传播和交往。
在交流阶段,研究生同学积极提问,何教授细致地回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并就相关议题进展开讨论,在场师生受益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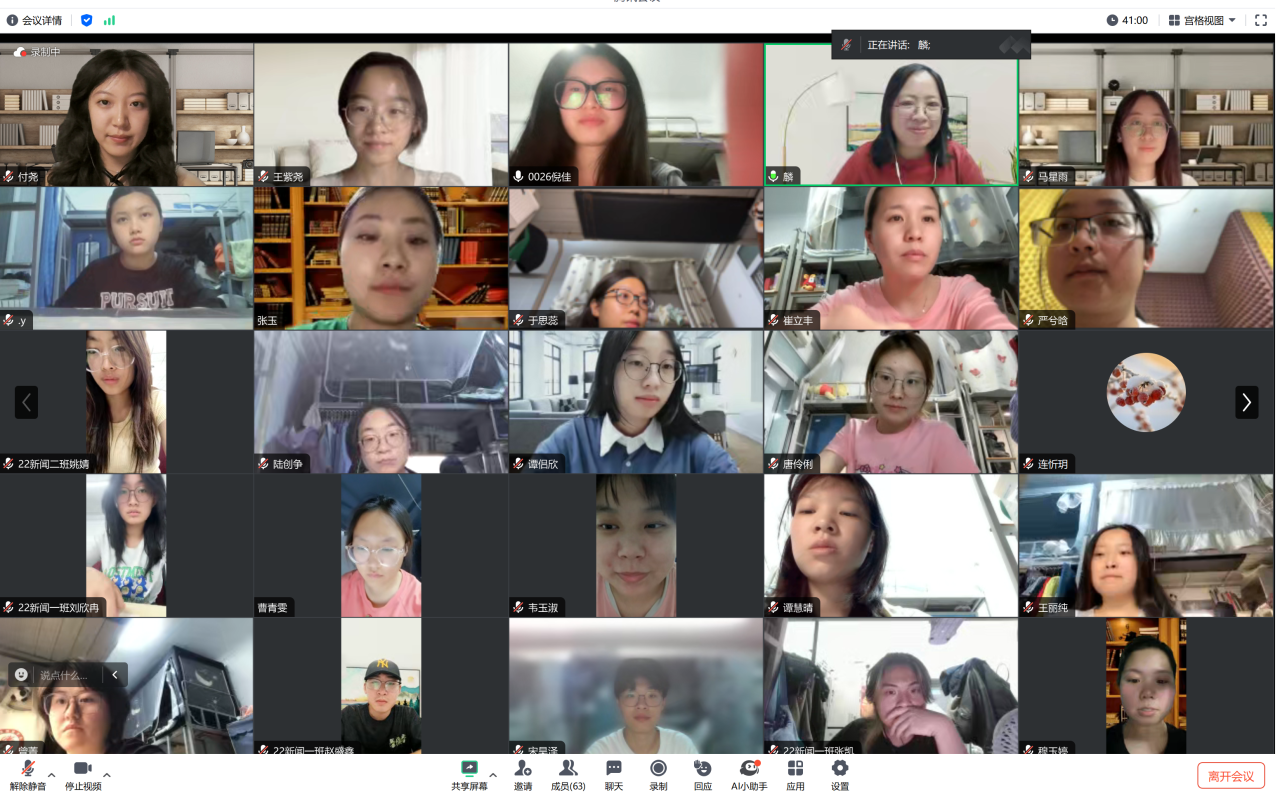
Copyright© 2020 文化传播学院 All Rights Reserved

